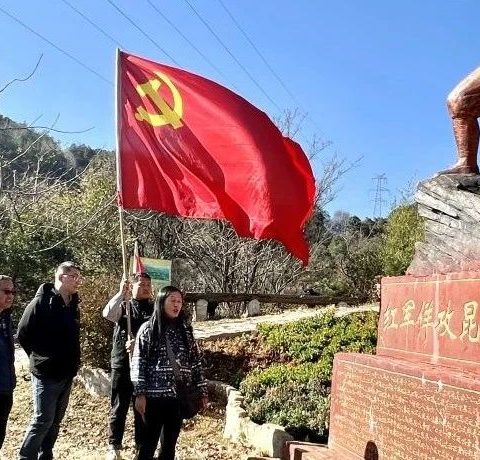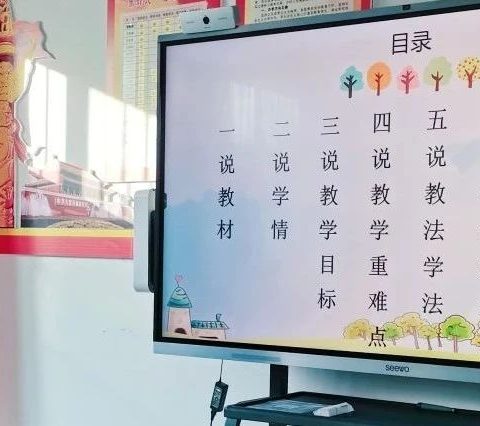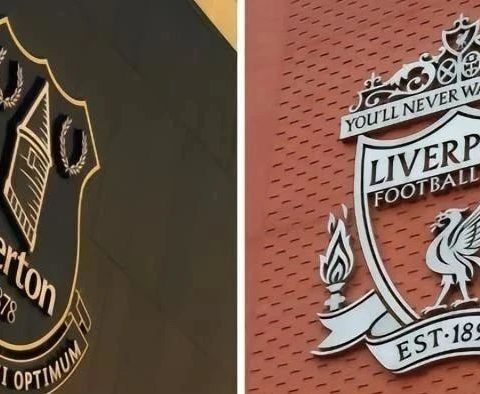1971年夏的一天,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乞丐站在位于济南市的济南军区司令部大门口。
他衣衫褴褛,头发乱得就像杂草堆,浑身脏得就像刚从煤堆挖出来,身上的气味就像在垃圾箱里刚住过半个月。
“同志,我是杨得志司令的老部下,我想见见他。”老乞丐可怜巴巴地向年轻的卫兵说道。
这位战士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老乞丐真的曾经是杨得志将军麾下的一员勇将。
他是飞夺泸定桥的十八勇士之一。
他在腊子口救过杨得志上将的命。
他是红军的团长。
他是延安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。
如果没有意外,他在建国后应该被授予中将军衔!
那么,这位英雄到底是谁?
他因何沦落成了“乞丐”?
他的命运会因为找到杨得志上将而改变吗?
“李祥”
侯礼祥是湖北江陵人,1912年生人,上过4年私塾,在当地也算个文化人了。不过在他十几岁时,父母就相继去世,他只能自己出去闯荡,找条活路,碰巧遇到我党的同志看他可怜,接济了他,他就开始跟着干革命了。
侯礼祥
1928年,他到了江西根据地,转年就加入了红3军团,但登记的名字是“李祥”,这是为啥呢?
因为他在老家侯家台时,周围都是亲戚,全姓侯,大伙干脆都省事,直接喊名字。侯礼祥也一样,被人叫作礼祥,他参加革命时,也说顺了嘴,所以战友们一直以为他就叫“李祥”。
1928年3月,他入了党,介绍人是他的连长~彭绍辉(上将)。
彭绍辉上将
侯礼祥别看个子不大,但打仗挺狠,在红军开始长征时,他已经是红1方面军1师1团的1营长,他的团长就是杨得志(上将)。
杨得志上将
在我军的部队序列中,凡是占“1”的部队都是精锐,杨得志的1团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干的都是尖刀的活,而侯礼祥带的1营则是尖刀的刀尖。
杨得志同志十分肯定地记得是1营干部战士强渡大渡河,飞夺泸定桥,而带队的营级干部就有侯礼祥。不过,因为当时战斗频繁,军史把18勇士误记为17勇士,1970年代,侯礼祥和杨得志吃饭时,为了这个事还拍桌子发过火。
在红军北上陕北的最后一次大战~腊子口之战中,侯礼祥把负伤的杨得志从火线背了下来,然后哥俩拜了把兄弟。
侯礼祥是个挺乐观的人,大大咧咧。长征快结束时,他有一次帮红1军团宣传部的一位领导用石灰刷标语。领导笑着夸他的字不错。
他来了一句:“我是光写白字呀!”
领导疑惑:“你这字写得没错呀?”
侯礼祥哈哈大笑:“邓部长,这石灰写的字都是白的呀,你写的也是白字!”
小平同志闻听也跟着哈哈大笑:“你这小子挺会讲话嘛,叫什么名字?”
“我叫‘李祥’!”侯礼祥大大咧咧地回了一句。
小平同志
长征中,侯礼祥负伤5次,有一次子弹打穿了脖子,有一次右腿差点给打断了,等红军胜利会师后,他就在瓦窑堡的医院躺了一阵子,扥伤好了后,他当上了红1师13团的团长。这时候,杨得志已经调任红2师当师长,侯礼祥的新领导是师长陈赓(大将),政委杨勇(上将)。
杨勇上将
1937年,侯礼祥被调到延安“抗大”学习,过了几天难得的轻松日子,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,认识了很多新战友。
有一次吃饭的时候,他把打饭的饭勺藏了起来,气得一位战友把他帽子扔得老远,然后趁他捡帽子的时候,抢过了饭勺。侯礼祥也不吃亏,跑回来又把这位战友的帽子扔得老远,这下把光着脑袋的许世友(上将)气得粗眉倒竖,直瞪他,死也不给他饭勺,逗得其他战友哈哈大笑。
许世友上将
“抗大”毕业后,1938年初,侯礼祥开始在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,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。他离开警卫团后,杨得志还记得毛主席问过“‘李祥’去哪了?”
1939年初,在一次战斗中,他的大腿再次负伤,延安的条件艰苦,治疗得也差点,伤是好了,但行军打仗是没戏了。于是,组织上安排他回到地方工作。
当年底,他到了武汉“八办”,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,并把他介绍给我党在湖北的地下组织。随后,他被安排到老家江陵县,中心县委书记是魏西同志,负责接收了侯礼祥的所有组织关系。
身为红军团长,也算是衣锦还乡,但是老家却是日本鬼子占领的“白区”,侯礼祥没法透露自己的身份,只能把身份证明、残疾军人证放在从延安带回来的皮箱里,藏在床底下。
组织上对他有段考察时间,所以有一年没安排工作,所以他只能娶个老婆,开个牌馆先把日子过了。
好巧不巧,牌馆的人太杂,他被贼盯上了,皮箱也丢了,证明文件也都没了。侯礼祥气得把牌馆关了,3天就吃了一顿饭,原来打算伤养好了,拿着证明文件再回部队,现在可好,自己成了“黑人”,以后可怎么办?
“汉奸”
侯礼祥正郁闷的时候,组织上给他安排工作了。魏西同志让他以“侯文彬”的身份去监利县朱河镇“客串”“伪联保主任”,以便和当地的地下组织联系上,好打入敌人内部。
侯礼祥二话没说,把老婆往家里一扔就去了,可干了没几个月,当地被我党争取过来的伪县长叛变了,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。侯礼祥和其他同志奉命隐蔽,他也从此和组织上彻底失联,只能回到侯家台继续过老百姓的日子。
而组织上按他“李祥”的名字也没能再联系上他,于是就把他列为了“烈士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,侯礼祥觉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,就跟乡亲们说出了自己红军团长的身份,还经常讲长征中的各种战斗经历。但是,他没有证明呀,大伙也就认为他在吹牛,甚至把他当成了神经病。
侯礼祥本来就嘻嘻哈哈,也没把大伙的看法当回事,可过了几年,问题来了。什么问题呢?
他当过“汉奸”呀!
于是,侯礼祥成为了被专政的对象,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当时,“专政对象”也就是在组织上登个记,并没有强制措施,不过,侯礼祥心里还是老上火。
1961年9月,他无意间从旧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了老领导杨得志和杨勇被授衔的报道,简直是喜出望外,连忙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,说明了自己的情况,希望能军委能帮忙请两位首长为他证明一下。
几个月以后,喜闻他没死的杨得志和杨勇两位将军都给他写了亲笔信,侯礼祥嚎啕大哭。他按照来信的地址,又给两位领导写了“求援信”,同时把过去共同的革命经历也写了,方便领导鉴别他的真伪。随信,他还写了描写强渡大渡河的诗。
信发出去以后,侯礼祥琢磨有这两位名震天下的将军给自己做主,真相终于可以大白了!
但是,结果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
他拿着两位领导的亲笔信找到公社干部时,大伙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个长相都可以说有点“狰狞”的干巴老头和共和国的将军有关系。所以,他仍然被当成神经病。加上朱河镇的乡亲们还记得他当伪联保长时的“丑恶嘴脸”,于是,侯礼祥成了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。从此,他和杨得志和杨勇的联系也断了。
1971年5月份,在林场改造的侯礼祥已经年近六旬,他是恨死当初的那个小偷了,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说不清了。
俗话说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
有一天,他又看见了《人民日报》的一则消息:杨得志担任了济南军区的司令员。
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侯礼祥心里油然而生:我要去济南找老首长!
可从湖北到山东可谓千里迢迢,一穷二白的侯礼祥该怎么去呢?
老乞丐
侯礼祥不愧是老红军,在花甲之年又拿出来当初长征时的那股不怕死的劲头。
他从林场偷偷跑出来,徒步走到了50多公里外的沙市,用身上仅剩的2毛钱吃了一碗面后(1毛钱吃面,1毛钱当了粮票,饭店服务员看他可怜,没和他计较),搭上了去武汉的渡轮,管理员看他可怜也没找他收船票钱。
到了武汉,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,从武汉该怎么去济南呢?
没办法,侯礼祥豁出去的,60岁的老头子开始“扒火车”!
他当时都是从小车站扒敞篷的货运列车。这个货车虽然开得不快,但爬上2米来高的车厢也绝对是个技术活,小伙子都不见得能爬得利落,可侯礼祥就行。
货车的速度不快,但时速也超过了50公里,在车厢里吹一路风可不是好玩的。而且侯礼祥只能在晚上扒,大半夜经常把他冻得缩成了一团。
路上他要是饿了,就找当地的老百姓要口饭吃,实在不行,他就在田里摘几根黄瓜充饥。但是侯礼祥很诚实,还保留了老红军的作风,拿完黄瓜,还用树杈在地上给老乡留个言,告诉人家自己是谁,拿了几根黄瓜,等胜利之后一定赔偿,然后划拉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。
就这么一路实打实的风餐露宿,60岁的小老头终于一路“扒”到了济南,当他来到军区司令部门口时,就发生了文章开头时的一幕。可像他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邋遢乞丐,卫兵战士怎么敢随便通报给司令呢?
侯礼祥没办法,一直在大门口软磨硬泡,卫兵只能联系了值班室的刘文书。刘文书听了侯礼祥的自我介绍后,觉得此事非同小可,当时天色已晚,就先把他安排到附近的旅馆住下。
侯礼祥回忆当天他自己要求住了大通铺,结果睡觉时,他的臭脚把一屋子人都熏跑了,等服务员把他叫醒下床时,他躺过的床单上留下了一个人形大黑印。
第二天一早,刘文书向杨得志汇报了情况,杨司令闻之一惊,不过为了稳妥起见,他让刘文书亲自去找侯礼祥,看看他带没带过去的信件或者是证明材料,并且让他写一份情况说明,把往事写清楚,以便看看这人到底是不是“李祥”。
杨得志
侯礼祥的证明材料早就丢了,而且是偷着跑出来的,身上啥都没有,只能写情况说明。他寻思了大半天,写下了在1935年9月,他奉命保卫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事情,同时重点提到了周总理对他和杨得志的殷切期望。他的这段回忆后来被江陵党办整理出来,在解放军的《星火燎原》发表过。
当杨得志看到这份情况说明,并对比了侯礼祥过去来信的字迹后,命令刘文书:“跑步去把他给我叫来!”
当天晚上,在军区第一招待所里,杨得志司令带着好几位年轻的军长一块陪侯礼祥喝了一个天昏地暗。
后面的几天,杨得志让一位参谋带着侯礼祥在济南参观游览散散心,在他走之前,又他准备了吃喝穿戴两大包礼物,还有100元现金(当时的县委书记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)和20斤全国粮票。
更重要的是,参谋交给他一封杨得志的亲笔信,让他一定转交给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(中将),让曾司令帮助他找当地政府来恢复他的名誉和老红军身份。侯礼祥一听就问了一句:“是不是打腊子口时,我那营的副营长?”一句话把参谋听得目瞪口呆。
曾思玉中将
1973年12月,毛主席命令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,杨得志就是和曾思玉对调,然后当了武汉军区司令员。
1974年4月,杨得志视察到荆州,想起来好久没联系的侯礼祥,就问了荆州军分区的司令员粟侠辉一句:“侯礼祥在哪呀?”
老红军
粟司令被问得一头雾水,然后赶快安排人联系江陵县,随后一通折腾,终于找到了侯礼祥。当天晚上,杨得志、军分区的领导、江陵县的领导一块在军分局招待所等着他吃饭。
等看见侯礼祥的时候,杨得志拉着他的手向大伙介绍到:“在长征中,我负了伤,就是他把我背下来的!”随后,餐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但吃饭时,杨得志拍了桌子。他为啥生气呢?
杨得志
因为侯礼祥的事没解决。
为什么没解决呢?
因为当地组织部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,没有依据给侯礼祥恢复名誉。
听了当地领导干部的说明后,杨得志也消了气,嘱咐要按组织上的程序抓紧办理侯礼祥的事情。
为了侯礼祥这个事,杨得志、杨勇、魏西、宋任穷等几位老领导都提供了证明文件和帮助。
杨勇上将的证明信
杨得志上将的证明信
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开具的文件
魏西同志的证明信
侯礼祥的老红军团长身份终于得到了恢复,他还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,并享受每月40元的补贴和医药费报销的待遇。乡亲们终于相信他的话是真的,老头子也终于可以在家乡名正言顺地给晚辈们将革命故事了。
1991年,侯礼祥老人病逝。但他的英雄事迹,以及战友们和他之间的深厚革命情谊将永世流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