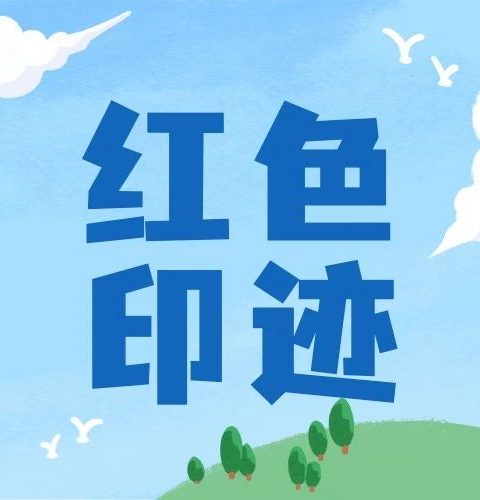引言
巴德玛是鄂托克前旗草原上最早觉醒的蒙古族妇女,投身革命以后,不论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,还是在和平环境里,她都积极工作,始终坚持信仰。她和一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学习,和同志们一起深入草原,宣传党的民族政策,与敌人机智周旋,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
布拉格草原绿草如茵,鲜花盛开的季节里,伴着嘹亮的哭声,一个女孩呱呱坠地。母亲诺敏给她的掌上明珠取了个好听的名字-巴德玛。巴德玛从小聪明懂事,放羊、挤奶、扫粪,做家务都是一把好手。大家都很喜欢她。
巴德玛的爷爷在草原上深受大家爱戴,他常常为当地牧民鸣不平,让那些封建王公不敢肆意欺压百姓,这给巴德玛从小的心灵种下正义的火种。
抗日战争时期,党中央委派李占胜、高义德等政治工作人员来到三段地,住在姚仓家,以蒙民招待所为掩护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工作。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,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,也吸引了一些蒙古族进步人士,巴德玛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一天,巴德玛一边放羊一边纳鞋底,看到好朋友傅银花向她走来,说:“听说三段地有个识字班,不光教人识字,还能听到许多新鲜的事,你去不去?”巴德玛说:“我也听说了,正想找你呢,我给阿妈说一声,咱们一起去。”在三段地工委,巴德玛和傅银花学到了很多的革命道理,知道了八路军是为人民做事,替穷人说话的。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络组,联络点就设在傅银花的家。
红色“1+6”
各种势力在鄂托克西部草原上横行,他们修建据点,建立防御工事,欺压老百姓,强征马匹,抢夺牛羊和粮食。鬼子、伪军、土匪还有一些地方势力,他们走在哪里,都是鸡飞狗跳,不得安宁。巴德玛的家里也同样遭到敌人的掠夺,家里没有了粮食,靠挖苦菜,揪沙葱和着风干的死马、死羊肉过日子。更为不幸的是爷爷和爸爸这两位家里的顶梁柱相继去世,让这个贫穷的牧民家庭雪上加霜。敌人的暴行,激起了草原牧民们的仇恨,三段地工委的地下党向一些进步青年宣传当前形势,动员他们起来反抗。巴德玛也逐步走向革命道路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巴德玛和一些进步青年去定边参加了抗日游行,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心,觉得只有跟着共产党,穷人才能翻身。
巴德玛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,她和傅银花常常一起聊天,她们非常向往延安,想去当红军。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母亲,母亲说:“女儿呀,咱穷人就是穷命,认命吧”。巴德玛就给母亲讲她在三段地工委听到的新鲜事。母亲担心地说:“女孩子家的,出去抛头露面,人家会笑话的。”巴德玛耐心给母亲讲:“如果我们不去反抗,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”母亲答应了她的请求。
她和杨宝山、贺什格达赖,六斤、乌力吉扎尔嘎拉等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奔赴延安。而傅银花却因为家里极力反对没有成行,巴德玛成了伊克昭盟地区唯一在延安求学的女青年。党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见到他们后,希望他们留在延安党校学习,一起同去延安的个别同伴对组织的安排有些不理解。他对巴德玛、杨宝山说:“学那个政治、文化有什么用啊?还不如扛着枪直接回家闹革命痛快!”杨宝山和巴德玛却有不同的看法,他们觉得党中央这么重视少数民族工作,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,政治水平也不高,需要好好学习,将来能够报答党和人民,是件很光荣的事。经过他们的劝说和组织部同志的开导,他们一起去了延安桥儿沟,住进了延安党校,编进了民族班。
延安的一切都让巴德玛感到新鲜和稀奇,她穿起了灰布制服,戴上八角帽、扎着腰带,剪掉了陪伴她多年的长辫子,脱掉了长袍,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。窑洞前的小院就是课堂,墙壁上挂着小黑板,每人发一个小板凳,大家坐在院子里认真听老师讲课。对于边远落后的牧区的蒙古族妇女来说,能在延安的最高学府参加这样的学习,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,巴德玛很珍惜。巴德玛只在家乡学了几个字,到了这里感觉自己学习起来很吃力,课后,她总是虚心地向别的学员请教,她的理论水平和军事技术提高很快。这一年里,他们学习中共党史、游击战争、统一战线、民族战争等知识,还参加军事技能训练,巴德玛如饥似渴地探索革命理论。她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劳动,自己纺纱织布,捻毛线,开荒种地,在延河边自由自在地散步。她还和学员们一起看电影,打排球,参加了文艺宣传队,学习紧张而又生动,让她几乎忘记了一切。
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家乡日日盼望自己的独生女儿能早点回来。逢人就捎话,她很想念女儿。正在学习的巴德玛,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,吃不香,睡不着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她向领导汇报思想:”我受到党的教育,学习了革命理论,应该对党有所作为。可是母亲的来信让我坐卧不安。领导让她静下心来坚持学习。
一边是学习,一边是母亲,她都难割舍,无奈之下她又去找领导:“从我的家庭实际情况来看,继续留在延安有困难,我打算回到家乡闹革命。”领导答考虑再三。答应了她的请求。
回到家乡,她积极向乡亲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,许多进步人士向她靠拢,她的家就成了秘密宣传点。
她带领苏力克木、巴音敖其尔、丹德尔,那仁特古斯等进步人士来到定边,受到三边地委书记高峰的热情接待。三边地委的领导向这些进步人士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,还和他们结为兄弟。巴德玛代表边区人民给力克木、巴音敖其尔、丹德尔,那仁特古斯摆上羊背子,用蒙古族的最高礼节热情款待他们。
红色“1+6”
有一回,巴德玛穿着灰军装从定边回到布拉格探望母亲,乡亲们见了很是稀罕,都称她“红军巴德玛”。看完母亲后,巴德玛急切地来到傅银花家,打算看她曾经的好伙伴。可惜的是,傅银花家大门紧闭。母亲告诉巴德玛,傅银花如今成了齐恩诚的第三房姨太太,穿金戴银,吃香喝辣。巴德玛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,就和我党地下工作者商量应对办法。于是,根据上级的指示,巴德玛就将计就计,说自己受不了苦逃跑回家的。
果然有一天,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地方头目章文轩想敲诈巴德玛,就把巴德玛和她的丈夫宝日浩道抓去。章文轩问:“你跟红军有什么关系?你的亲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?”巴德玛说:“我是参加过红军,可是那里太苦了,我就逃跑回了草原”。章文轩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,急红了眼:“你们家有哪些财产?”巴德玛说:“我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,野外有一匹瘦马,一头牛,家里有患病的老母亲和我。要打有屁股,要站有两条腿。”章文轩觉得问不出什么,又没什么油水可捞,认为巴德玛就是一个红军的逃兵,打了夫妻俩几鞭子就放了他们。
从此,巴德玛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,与革命队伍的联系也更密切了。革命宣传工作也更加秘密而紧张。
改编:薛金丽
教育工作者 文学、国画爱好者,《鄂尔多斯作家协会》会员,《西部散文协会》会员,《红柳河》责任编辑。文章散见于《鄂尔多斯日报》《西部散文选刊》,学习强国等平台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消逝的季节河》。
编辑|张 峰
终审|薛金丽
《红柳河》374期
邮箱:3197466474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