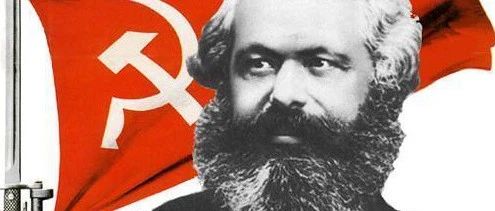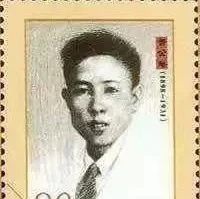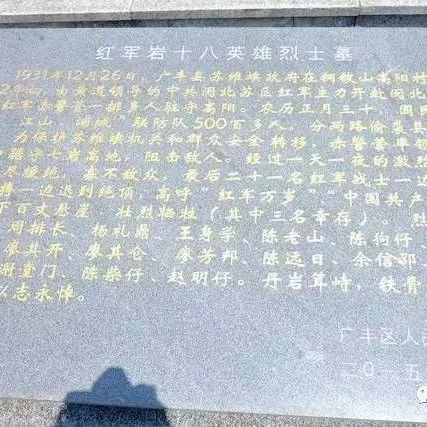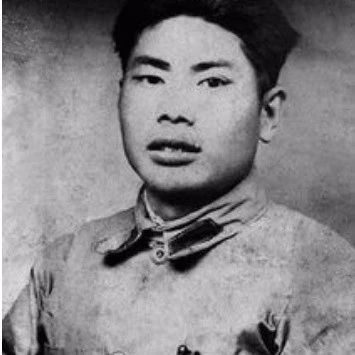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,毛泽东从一个勇敢的民族主义者,转变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!
一、虽然自己立足于囯内。但,支持恰同学少年们出洋留学。
1918年6月,恩师杨昌济于北京来信与学生毛泽东:
1912初,由众多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教育界人士,如,蔡元培、李石曾、吴稚晖、吴玉章等人,他们发出了在北京组织“留法俭学会”的倡议,鼓励青年才俊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,达到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的目的,以图彻底的改良中国社会。
此信,令毛泽东大受启发,深以为然,认为这是一个救国之良策,随即同何叔衡、蔡和森、萧子升等组织召开“新民学会”会议,商讨此事。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,最后一致认为:
赴法留学意义重大,必须尽快做好筹备工作,并推举蔡和森、萧子升专负此责。
“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,组织预备班,出力甚多,才智学业最为同学所佩服。”
在留学成为时尚、甚至是时髦之时刻,毛泽东秉持首先要了解中国,然后,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态度,无论是当时,还是时下,都足可谓是惊世骇俗的。这也是他最终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卓越的真知灼见。
对于南方青年而言,北方的冬天来得似乎格外的早,寒冷异常。北京的生活费比长沙高许多,他们不得不以玉米糊、窝窝头、咸菜等度日;就买煤烧炕一项,就足以掏尽每个人的腰包,每人若能买上一件棉大衣,那是奢侈的不得了的事情。
众人中,毛泽东最忙,为了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四处奔波。据说,毛泽东还因生活窘迫,三九天只好靠经常吸烟和吃辣椒御寒。
蔡元培写了张条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,说:
“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,想在校内做事,请安插他在图书馆。”
毛泽东后来追忆道:
“我的工作很糟,人们都不愿意跟我讲话。”
是的,在人们的眼中,图书馆助理员是微不足道的、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位。谁愿意去搭理这个来自湖南的“土里土气”的青年呢?
为了开展湖南的群众运动,迅速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,保持他们的斗争热情,也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能昭示天下,毛泽东觉得,在长沙办一个专刊很有必要。于是,1919年7月14日,《湘江评论》横空出世。
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撰写的最重要的文章,就是长篇论文——《民众的大联合》。文中,他礼赞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,主要论述了人民必须联合、团结、组织起来的极端重要性。
毛泽东第二次来京的目的——争取全国、特别是北京各界的名流对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支持。因此,1919年12月18日,毛泽东一经来到北京,就立即和湖南代表团成员一起奔走呼号。
这次“驱张”活动,各种“驱张”的电报、通电和新闻,雪片般地飞向全国,毛泽东的名字也频繁地出现在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。湖南的“驱张”运动,以学生们的胜利而告结束,毛泽东的领导能力、毛泽东的政治诉求,通过这次运动,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和重视。
毛泽东再次来京,这让苦苦思念的杨开慧热泪长流。天涯海角热恋的一对,终于又可以形影朝夕了。激动之余,杨开慧炽热而真挚的感情告白,一行行地跃然于纸上:
“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!得到了一个爱人。我是十分爱他。”
在埃德加·斯诺记载在《西行漫记》中。
毛泽东如此表白:
“到1920年夏天,在理论上,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,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,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1920年5月5日,27岁的毛泽东来到上海,在位于安义路上的一幢两层小楼上住了两个月。刚到上海三天,即5月8日,他就和旅沪的“新民学会”会员在半淞园会面,商讨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大事。
此时此刻,陈独秀同李达、李汉俊等正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。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,与陈独秀促膝长谈。
毛泽东后来向埃德加·斯诺追忆道:
“我第二次来到上海之时,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。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,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,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”
1921年7月,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,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——中共一大。他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老成持重、沉默寡言,虽“很少发言,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”。
那一时刻,如此年轻的毛泽东就曾向好友萧子升信心满满地预言道:
“假如我们努力奋斗,再过三、五十年,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”。
以三十年后的1951年为例,苍茫大地己给出了答案——毛泽东主宰中国的沉浮。
谨以1951年4件大事为例:
1、1月21日: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首次与美国空军激战。
2、2月18日:中央提出“三年恢复,十年建设”之规划。
3、5月21日:与巴基斯坦建交。
4、8月15日:周恩来重申中国对南沙的主权。
补叙一段佳话:
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资金,即使采取半工半读的最省钱方式出国也仍然如此。
此事并没有难倒毛泽东,毛泽东求助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。杨昌济将毛泽东和蔡和森引荐给自己的挚友,当时在北洋政府中颇有影响力的章士钊先生,他在信中写道:
“吾郑重语君:毛、蔡海内人才,前程远大,君不言救国则已,救国必须先重二子。二子当代英才,望善视之!”
毛泽东拿着杨昌济的信只身赴章士钊处,简短寒暄后,直白来意,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,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,不久便募集了大洋两万块。毛泽东在回忆里写道:
“1920年5月到了上海后,我才知道(章士钊)已募有一大笔款子(两万银元)资助学生留法,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革命。”
资料载:
【两万大洋相当于现在的150万左右的人民币】
章士钊的慷慨义举,主席一直铭记于心——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回忆:
“1964年初,主席读完英文之后,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……主席突然我:‘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,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?’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,我说父亲没有讲过。要是主席欠债,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。主席却很认真地说:
‘也许行老忘了。这笔债早该还了!’主席说:
‘你回去告诉行老,从现在始,我还他这笔欠债,一年还2000元,10年还完
2万。’”几天之后, 章士钊果然收到了主席派秘书送来的第一笔钱2000元。章士钊要女儿转告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, 并说当年这些钱都是募捐来的。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泽东时,毛泽东笑了:
“你也不懂,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”。
1971年春节, 主席见到章含之时突然问:“今年的钱送去没有?”当得知两万元已还清没有再送时, 毛主席笑着对章含之说:“怪我没说清, 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, 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, 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。你回去告诉行老,从今年开始还利息。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, 就这样还下去, 行老只要健在, 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。”
就这样,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,直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。
二、马克思主义成了毛泽东的终生信仰。
旧中国主权沦丧,吏治腐败,生灵涂炭,中华民族灭种之危迫在眉睫。为救亡图存,毛泽东苦苦探索。在读书求知与革命实践中,毛泽东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,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少年中国说时的毛泽东“身无分文,心忧天下”,列强的碾压,军阀的顽固,社会的反动,使他痛如切肤:“国家坏到了极处,人类苦到了极处,社会黑暗到了极处”。他立志,寻求一条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之路。
毛泽东对民族处境万分忧虑,他仰天长啸:“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、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”。
1915年5月,为抗议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,人们将5月7日确定为“国耻日”。毛泽东愤然挥笔疾书:
“五月七日,民国奇耻;何以报仇?在我学子!”以此表达对袁世凯卖国行径的极大愤慨,勇担当、雪国耻之豪情,跃然纸上,溢于言表。毛泽东认为要救国,青年人要堪当大任,立大志,关心世界大事。他号召大家共同行动,彻底改造旧中国。
封建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桎梏,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。毛泽东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,必须先摧毁旧文化,使封建文化抽心一烂;大破大立,移风易俗,开启民智,刮骨疗毒,再造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图腾——“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”。
文化,是一个民族大脑里的芯片,毛泽东对旧中国腐朽落后的反动封建文化深恶痛绝,他尖锐的指出:
“五千年流传到今,种根甚深、结蒂甚固,非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”。特别是1919年11月,长沙发生赵五贞女士抗婚自杀事件,社会反响剧烈。毛泽东连发10篇评论文章,抨击反动的封建文化和由此孽生的封建制度,他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。
1919年7月,毛泽东任主编的《湘江评论》创刊,该报旗帜鲜明:
“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。”创刊号共发表25篇杂文,22篇毛泽东主笔。毛泽东不遗余力批判旧思想、旧文化,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众的联合力量——试图把散沙拧成钢丝绳。号召人民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去冲破封建文化的罗网。毛泽东烈火般的工作热情启发了民众的思想,激活了民众的觉悟,也促使他自己的头脑得到武装,从而探寻出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。
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,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,必须联合志同道合者共同奋斗。那一时刻,毛泽东结识了一大批青年才俊,他们“集合同志,创造新环境,为共同的活动”架桥引路。
1915年秋,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发出“征友启事”,希望结交对学问、时政感兴趣,能刻苦耐劳、意志坚定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朋友。
启事发出后,李立三、罗章龙等人立即响应。罗章龙还和毛泽东通信约见。1918年4月,毛泽东提议创立的“新民学会”在长沙成立,这是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的集合,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团体,学会以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为主旨,要求会员作到五不:
不虚伪、不懒惰、不浪费、不赌博、不狎妓。
试图通过对旧中国个人品质的回天再造,重建个人操守,进而改造全社会。彻底的解决中国问题,学会成立后,毛泽东主张会员:
“都要存一个‘向外发展’的志”,走出去从实践中获取本领,毛泽东言行一致,他号召“新民学会”会员赴法勤工俭学。并于1919年1月在北京参加李大钊等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。4月,毛泽东回到故里,“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”。
不久,“五四运动”爆发,毛泽东看到了革命的火种,于是,勇敢地站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的最前列,与彭璜等同学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,组织学生开展斗争。
在参加和领导斗争实践中,毛泽东初步积累了经验,认识到了民众的伟力。但他也清醒地识到,运动虽然轰轰烈烈,但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,还相去甚远,救国救民必须有科学的大道理加持。当然,也包括对自己的指引。
为了探寻真理,毛泽东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时事和社会的问题。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动剧烈,新旧思潮相互碰撞,他的思想也在快速的变化之中。
1910年秋,在湘乡,县立东山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梁启超主办的《新民丛报》,开始“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”,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。
次年春,毛泽东考入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后,阅览了同盟会的《民立报》,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政治主张。
1911年他加入新军,参加辛亥革命,怀着浓厚的兴趣去探讨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。此后,毛泽东还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献,接受了进化论和民主思想。这一时期,改良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目不瑕接,甚嚣尘上,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毛泽东,那时候的毛泽东思想,“是自由主义、民权主义、民族主义、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等理念的大杂烩”。
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比较。各种主义主张处处碰壁的现实,令他逐步认识到要改变中国,必须有“另辟道路,另造环境一法”,觅到真知方可。
“主义譬如一面旗子,旗子立起了,大家才有所指望,才知所趋赴”
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,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疾风骤雨般的传播,毛泽东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”。
1918年8月,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,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。他阅读李大钊的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,广泛地接触学者,研讨各种社会主义的学说。他参加北大哲学会、新闻学研究会和“平民教育演讲团”的活动,实地到长辛店调查,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状况。
1918年的北京之行,是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。
1920年春,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,这一次他阅读到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《阶级斗争》《社会主义史》等书籍,他的宇宙观、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—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,从而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中革命量身定做的,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,马克思主义,是惟一正确之路。
从此,毛泽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,在湖南秘密开展建党活动。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:
“到了1920年夏天,在理论上,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,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如此,毛泽东终于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