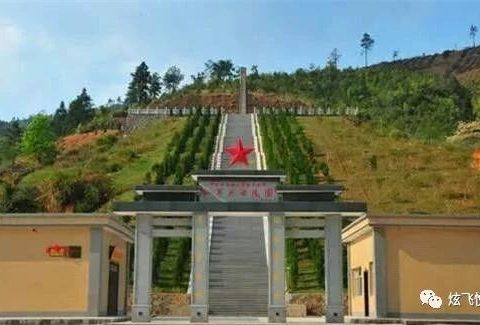《增广贤文》中有句谚语:打虎还得亲兄弟,上阵须教父子兵。意思是打虎要像兄弟一样一起向前,没有异心,就像手与脚相互配合一致,团结紧密才无往不胜。而上阵打仗则要像父子一样有长幼次序,忠心耿耿。临阵不退缩!敌人也从内部分解不了,父子兵就是铁板一块。因此,亲兄弟和父子兵可谓中军队中的最佳组合。自古及今,亲兄弟和父子兵在战争中叱咤风云,立下赫赫战功者不鲜见,双双成为令人敬仰的大英雄人物很多。
红军兵工厂旧址
在上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,为了民族的解放、人民的翻身,许许多多革命先辈投身武装斗争,有些是一家人都上阵,可谓是满门忠烈,有些兄弟齐上阵,都戴上了军功章。今天我们介绍俩兄弟参加红军,后来在残酷的突围作争中,兄弟打散分开,哥哥冲出去成为开国少将,而弟弟受伤被俘后回老家种田的故事,读来令人嘘唏不已。那便是江西兴国的刘玉堂(原名刘金启)将军和他的弟弟刘兰启。
不久前,笔者特意来到兴国长岗乡合富村文村村小组,特意去采访留在老家务家一辈子,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红军刘兰启。这里距离乡政府驻地有五六里地,周围有众多奇峰异岭,如竹笋峰、仙桃峰、蛤蟆石、芒锤石、读书岩等,风光秀丽,沿途看到的一条条平整的水泥路连通家家户户,一排排别墅式的漂亮新居错落有致,一个个蔬菜大棚集中连片。
一见到老红军刘兰启,他开门见山就说,解放前家乡是属于穷乡僻壤,他的家庭就是村里最穷的,他周岁丧父,8岁丧母,小小年纪成为放牛娃,经常在山涧沟坳里弄点野果子吃。他十来岁的时候,老家来了红军队伍,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办学堂,穷人翻了身,他这样的穷孩子便进了学堂,随后,他参加村里的儿童团,手里持头木头做的红缨枪,站岗放哨查路条,破除迷信搞宣传,大家革命热情非常高涨。
红军要扩大队伍,村里很多人都参加了红军,他的哥哥刘玉堂成为红军的一名地方干部,宣传扩大红军少共国际师,大家都高唱着:我们是少共国际师,坚决地、勇敢地武装上前线,做一名英勇无敌红色战斗员,最后的一滴血,为着新中国……威武雄壮地开赴反“围剿”前线。
这个时候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,刘兰启的哥哥刘玉堂在少共国际师工作,并奉命留守苏区,便跟着他去参加红军,一开始的时候是勤务兵,后来当通讯员,跟着留守在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师,起初,红十六师很强大,在通山、崇阳、修水、平江等地,一举摧毁国敌军在湘鄂赣游击区边界构筑的碉堡封锁线,向鄂东南行动。此时,敌人恼羞成怒,调集数十个团的重兵分布湘鄂赣,“进剿”以平江虹桥为中心的游击区,为了保存有生力量,决定突围转移。
在这一阶段,是非常的艰苦,断粮断盐断药,缺衣少食,还没有弹药。一身破衣干了湿,湿了干。刘兰启一直跟着哥哥刘玉堂,那一年刚好过年,大年三十那一天,他们转移到一座大山上,领导说大家辛苦了一年,就座在一起吃个年夜饭,便在山上找了一个“香菇客”丢弃的草棚,铺开一块布当餐桌,只见端上来只有二道菜:蕃薯丝煮野菜。
当年只有十多岁的刘兰启正长身体,好几个月不知肉味的他,本来想在过年的时候憋足劲吃上一顿鸡鸭鱼肉,解解馋,没有想到啥也没有。便发牢骚说:“哥,今天叫花子都有年饭吃,我们当红军,却要吃猪食。”刘玉堂瞪他一眼,训斥道:“乱说话,你扰乱军心!以后再敢这样说话,我就枪毙你。”吓得他赶紧承认错误,作了检讨。这件发牢骚事件后,刘玉堂把刘兰启调到红军部队的兵工厂去当工人,兵工厂分配做修理工,修理枪支。没有枪支修理的时候就生产“退子钩”,当时游击队的步枪比较旧,开了二枪后弹壳不会自动弹出来,要用一个铁钩子把弹壳钩出来,才能接着打,这种铁钩必须人手一把,故名“退子钩”。
那时,兵工厂也不是固定地点,而是抬着机器转移。情况紧急时,便把机器藏在山上,敌人“围剿”结束后,再把机器找出来继续生产。紧接着,敌人正规军及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的保安团,围攻湘鄂赣苏区,务必一举扑灭,面临十多万敌军步步紧逼,层层包围的不利形势,红军游队领导决定转移到幕阜山麦市镇突围,史称“麦市突围”。
此时,刘兰启跟着哥哥刘玉堂以及红军部队,进行紧急转移,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,我部开始行动,上级要求大家突围时要不说话、不掉队,不吸烟、不开手电。然而,还是被敌人发现,此时,敌人恃其优势兵力,以堡垒为掩护,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,弹如雨下。接着,敌人从后面包抄过来,象疯狗似的乱叫乱窜,我英勇的红军战士无不以一当十,勇敢杀敌,一时损失惨重,形势十分危急。在大家的奋力拼搏下,刘玉堂率领部分人马总算顺利地跳出了包围圈。
刘玉堂突围出去后不久抗战爆发,他作为湘鄂赣省红军和平谈判代表,前往武汉等地举行谈判,后任湘赣游击支队副司令员,将队伍改编新四军第一团奔赴抗战前线,后赴延安学习留校当班主任,中组织部晋西南巡视团团长、青工会军事体育部副部长等职。解放战争时先后担任独立团团长、吉黑纵队大队政治委员、吉林军区直工部部长四野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。参加了辽沈、进军西南等战役战斗,建国后武汉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,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然而,在突围中跟随着兵工厂的刘兰启,转移到一个山坳时,被大队的敌人发现了,在山坳两边开枪封锁,领导命令冲过去,大家便分散冲过去,刘兰启身前身后的战友都中弹倒下了,他闭着眼晴拼命跑,虽然受了点小伤,和几个战友居然冲过去了,然而抬头一看,竟然跑到敌人老窠里去了,这个镇子周围都是旷野,他们只好顺着沟渠慢慢爬,爬到天黑,但还是被搜山的敌人抓住了。
由于被抓住的时候,大家只说是在工厂里做工的,敌人一看也的确不象什么当官的,只是普通的工人,只罚他们做了一阵苦工,便押解回了原籍。他便回到了家乡安心地种田,由于后来老家成了白区,自此,刘兰启和哥哥刘玉堂也从来没有联系过。
直到建国后,刘兰启才听说哥哥刘玉堂在武汉做了将军,非常兴奋,便日夜兼程千辛万苦来到武汉的中南军区后勤部驻地,终于见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哥哥,刘玉堂一见面就十分惊奇地说:“你还活着,我还以为你在那次突围中牺牲了呢。”
刘兰启把离开后的全部情况向哥哥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汇报,随后便对哥哥说,你现在这么大的官,又是和平年代条件好了,就把我照样安排在你的身边工作吧。
随知哥哥刘玉堂告诉他:“你没有文化,当年红军连通信员都当不好,还是赶快回家去参加土地改革。我们当年革命不就是为了有几亩田种吗。在家里好好生产,支援建设。” 刘兰启老老实实回到家里务农,直到晚年。一辈子在他种田的他心态非常平稳,在老家经常唱着红军时期的歌曲,并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逝世的哥哥刘玉堂。没有事时经常到县城将军广场抚摸哥哥的雕像。
【免责声明】:转载自其他平台或媒体的文章,本平台将注明来源及作者,但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、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,仅作参考。本公众号只用与学习、欣赏、不用于任何商业盈利、如有侵权,请联系本平台并提供相关书页证明,本平台将更正来源及作者或依据著作权人意见删除该文,并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。